姬中宪,作家,大学老师,1996年进入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社会学系读书。曾是中国第一代专职社工,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出版长篇小说《花言》《我不爱你》《阑尾》,短篇小说集《一二三四舞》,非虚构小说《缓慢而永远》,杂文集《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今天》《时代文学》《天涯》《芙蓉》等发表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思南》转载,作品曾入选《南方周末》2007年度推荐书目,获首届华语文学创作笔会最佳小说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中峻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最佳读者印象奖、腾讯“瞬间与永恒”短小说大赛第一名等。2015年“姬中宪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作品以其鲜明的后现代城市文学特质与社会学视角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人物采访:
问:请问您在学院读书期间,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您认为四年的本科学习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说一件和专业有关的:大二时我们班接了一个大项目,替国家某部门做问卷调查,那个调查非常复杂,问卷是厚厚的一本册子,认真做完要花一个小时,要求入户调查,抽样也非常严格,抽到哪家就是哪家,同一家庭,抽到哪个人就只能哪个人做问卷,不能随便换,难度很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班全体动员,大冬天的晚上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济南市,一家一家去敲门。放在今天,这简直不可能,但是当时民风淳朴,绝大多数人家都为我们开了门,听说我们是山大社会学系的学生,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或者放下手里的筷子(我们经常趁晚饭时间敲门),给我们做问卷。因为要入户,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安全问题,所以一般是两人一组,男女搭配(我们班正好20个男生20个女生),男生负责女生安全,女生则负责让人家觉得安全,毕竟如果男生敲门,人家可能不敢开门,女生的话就好很多。我记得有一天深夜,还差最后一份问卷没完成,我和张军霞饥寒交迫,敲开了工人新村的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位阿姨,听说我们是大学生,不但满口答应做问卷,还给我们每人下了一碗面,每一碗面里都卧了一个蛋。我们吃面的时候,阿姨告诉我们,她儿子和我们同龄,在北京读大学,有一年从北京骑自行车回到济南,人晒得像个黑球,她一看到我们就想到了儿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阿姨的这碗面、这份情谊让我一直记到今天,这次调研不但是专业技能的一次演练,更让我们收获了人间冷暖。
也遭遇过误解,有一晚我们敲开一扇门,一大家子正聚餐,我们费了许多口舌说服他们接受调研,刚坐下来,门外突然有人大喊“抓贼!”,所有人都涌出去,原来是他们家放在楼道的自行车被人偷了,一家人迅速分成两组,一组去抓贼,另一组却将矛头对准了我们——他们怀疑我们和贼是一伙的,里应外合,这边拿问卷吸引他们注意力,那边伺机下手。那一刻我们被他们团团围住,真是百口莫辩。万幸,我们手里有学院的介绍信,信上盖着大红章,进小区时给门卫出示过,自行车也很快被追回来了,误会澄清了,那家人也觉得不好意思,问卷做得格外仔细。这样的情节无论如何都预想不到,但这就是社会调查的魅力,这就是人间真实。
四年的本科学习深深地形塑了我,从内到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是,它让我确立了一个标准,即用审美的而非纯实用的标准来评判万物、训练自我,而美的最高标准是真实,审美即求真。母校在我心目中始终是纯粹的,超拔的,没有对这个世界亦步亦趋,更没有低头示好,“我是山大出来的”,每当我要沉沦时,这句话会激励我。本科四年正是一个青年确立三观的关键时期,标准一经形成,就很难再降下来,这是我的人生底色,我受用至今,感谢宁静、古朴的山大老校,帮我把底色明确和固定下来。

问:在校期间有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在您读书期间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读书时我非常内向和社恐,但是我的性格又属于人畜无害型的,所以在班里人缘挺好,尤其在男生中间,跟谁都能说说笑笑。我们班男生有三个宿舍,分别是505、506、507,为了不显得厚此薄彼,我每个宿舍选一个代表(没选到的别生气):505的郑永强,他是我们中最文艺也最洋气的一个,那时候就弹吉他,听涅磐、皇后、碎南瓜,而我当时只能听听中国本土的二手摇滚。郑老师而且能写会画,自弹自唱,甩我们这些半吊子文艺男好几条街,毕业近二十年后,我去美国找他,一起开车游历,和同车年轻人聊起大学生活,我还说过:论才华,我远不及郑老师,我只不过是坚持了下来。506的王恩界,我的室友,我们朝夕相处四年,互相更知根知底一些,不管多久没见,见了也不需要预热,一秒就能找回当年的状态。恩界文武双全,一身绝学,是我们的组织后卫,我们的段子手,永远能和我们细声细语说些心事的好伙伴,2000年毕业前夕,我去上海参加研究生面试,恩界帮我拎着包,送我去校门口的公交车站,十八年后我去广西大学找他,王教授骑一辆小电驴载着我,校园里招摇过市,我在后座上搂住他的肩膀,我们好像还是二十岁上下,去自习的路上,谈论着乔丹、爱情还有种种人生快意与不如意。507的谷禾,和我一样少言寡语,心事重重,我们在人群中迅速辨认出彼此,一度同进同出,无所不谈。他画画很好,去青岛玩一圈回来,手绘“青岛印象”,绿树青山,红屋顶层层叠叠,至今想到青岛,还会想到他的那幅画。他文学造诣也颇深,我那时胡乱写几首诗,无人理睬,有一天去507,谷禾在上铺,幽幽开口:‘海生长在树上,就可以深不可测’,嗯,这句还不错——这是我在诗歌方面收到的为数不多的肯定。毕业后我们从未见过,虽然加了微信,互动极少,接近于零,但是有一天我翻唱了周云蓬的一首《沉默如谜的呼吸》,发在朋友圈,他罕见地点了赞。我知道,谷禾还是那个谷禾。
这就是青年时代选择的朋友,我想我们没有看错人,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们仍是同类人。2015年在内蒙,我和永强有一场对谈,台下有读者朋友问:这么多年过去,你觉得你们变了吗?我当时回答得不太满意,我想现在再回答一次:我们没变,我们只是隐藏得更深了。

问:在您就读期间对社会学系有着怎样的印象?有没有哪位老师让您印象深刻?
我对社会学系的印象是每位老师都很有个性,无论形象气质、言谈举止,辨识度和区别度都很高。今天我也是一位大学老师,和我当年的老师们相比,我觉得我和我的同事们要雷同和乏味的多,也许因为当年我涉世不深,看谁都新鲜,也许因为我们今天接受的教育和信息都太标准化了,以至于千人一面。具体来说,男老师里,吴忠民老师犀利,孟庆团老师正气,马广海老师俊朗,高鉴国老师洋气(言必谈 Canada),林聚任老师敦厚,泥安儒老师儒雅,王忠武老师亲切,葛忠明老师帅气,杨善民老师聪明,程胜利老师憨厚,像我们的学长……女老师里,李芹老师谆谆教导,是我们的第一位专业启蒙者,庄平老师睿智优雅,是我们的女神,赵慧珠老师身体力行,每周带我们去福利院做志愿者,万丽丽老师快人快语,她的理论课信息量最大也最虐人,傅艺娜老师温柔有爱,像我们的学姐,还有一位王小云老师教我们高等数学,毕业多年后才知道她是名震中外的密码专家,教我们这群文科生,真是大材小用了。大学贵在兼收并蓄,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些既富有学识,又葆有各自人格魅力的老师,他们不只是以专业代言人、更是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样子站在我们面前,遇见他们,是我们学生的福气。
问:您现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能否请您谈一下当初您开始写作时背后的故事?
我从小喜欢写作,小学时就有作文得奖,被印到书里,小学中学历任语文老师都在班上读过我的作文,但是真正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却是始于大学,山大浓浓的人文气息滋养了我,社会学专业的独特视角与社会关怀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特别的给养,让我在文学界与众不同,山大的开放包容也鼓励了初试写作的我,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一首长诗得了学校征文的首奖,然后有一天中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校园广播里突然开始朗读这首诗,声音从天上飘下来,从树梢和教学楼宿舍楼的楼顶倒灌下来,整个山大老校沐浴在我的诗歌里,我听了半天才敢相信那真是我写的,那一刻我又激动又着急,想把眼前的一切留存下来,却无能为力,只能打电话给我当时的同桌于江平,让她赶紧打开窗户听一听……
此外,在山大读书的四年里,还有这样几件小事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我的写作:大一时上计算机课,首次接触输入法,老师让我们在全拼、双拼、五笔中任选一种,我一时手欠,选了五笔——上手最难,可是一旦上手就非常快速的一种输入法。如今五笔已成为我手指的一部分,它规定了我的写作的基本语法,我曾说过,一个用全拼写作的作家和一个用五笔写作的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庆幸选了五笔,这是我成为一个作家的最重要的技术储备。第二件事是1997、1998年间,我们几个男同学凑钱攒了一台电脑,一台笨重的586,打游戏和看碟片的间隙,我开始尝试在电脑上写东西,这在我的私人写作史上不亚于原子弹的发明,我从此是一个有核作者而不是一个无核作者了。这件事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回头路,直到今天。放弃纸笔改用键盘,相当于人类进化史上的“直立行走”,变的不仅是介质,更是场域、视野的进化,是人与文字关系的一次重建,一开始非常不适,几乎要放弃,一旦调适得当,便如虎添翼。至此,成为一个作家的全部物质准备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只需要才华和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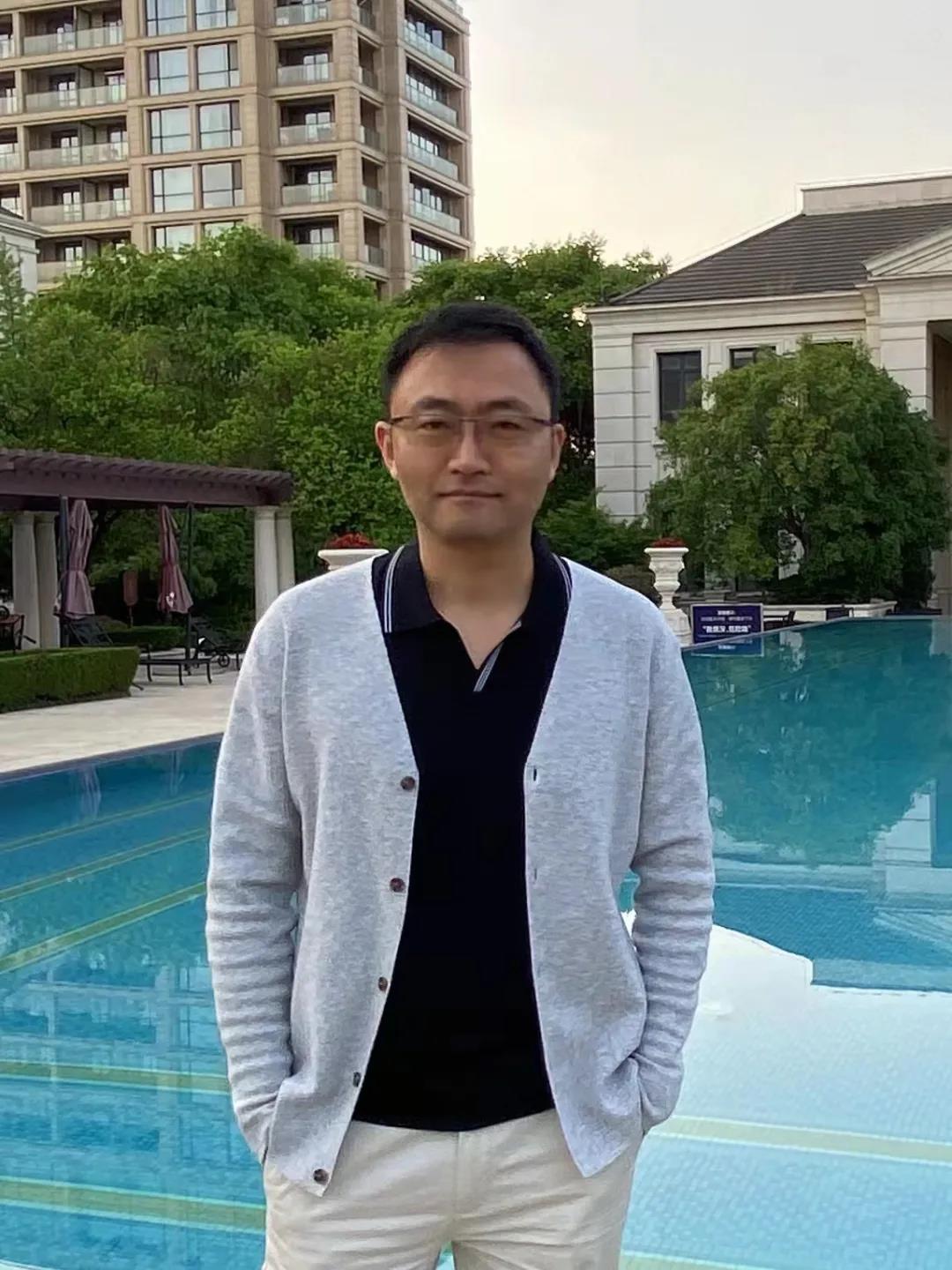
问:艺术源于生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生活经历、工作背景对您创作的影响呢?
从山大毕业后我去华东理工大学读研,读的还是社会学专业,方向是社会工作,毕业后在上海浦东从事社会工作,一做八年,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科班出身的社工。社工经历让我有机会大量接触社会,为写作准备了素材,我有一本杂文集《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就直接取材于此,还有一本非虚构小说《缓慢而永远》,写的虽然是身边人,但某种意义上也都可看作社工的服务对象。我在小说中也多次写到社工,写到社会百态、人间群像,小说是世俗土壤中开出的花朵,这段经历为我提供了土壤。另外,我的个性使我很容易成为一个纯粹的书斋中的人,社工经历逼我完成社会化,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我后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学老师,我的身上仍有许多“社会”习气,我为我身上的社会性骄傲,我觉得不管作家还是大学老师,首先都必须是一个社会人,必须以社会一分子而不是以社会的旁观者、体验者来观察和描摹社会。

问:您创作了多部小说,能否谈一下您最喜欢的作品?在写作和创作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记忆呢?
最喜欢的永远是最新的作品,所以就说一说我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花言》吧。这本书的简介中写道:这是一部长篇情书,也是一个人的半生漂泊史。但是这个人并非个案,而是代表了一群人、一代人,所以又具有了社会学的样本意义,相信每个人读过后都会有一些同感。在这部小说中我觉得自己有两点改变:一是有了感情,王朔曾经说过,“年轻人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感情。”我曾经也是一个冷酷的写作者,但是人到中年,我开始有了一些感情,在《花言》中甚至有些感情泛滥,几近失控。二是重新调整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纯粹私人视角、私人语气讲述故事。过去,社会学的教育背景曾让我的文学写作受益,但同样给我带来局限,毕竟社会学不等于文学,在社会学中,我们言必谈社会,但在文学写作中,必须将抽象的社会内化进具体的个人,因为在文学眼中,个人之外,并无社会,个人就是社会。
《花言》中多次写到济南和山大,我动用了山大四年期间关于济南的全部记忆,而位于济南东北的山大老校,是这段记忆的中心。我摘录几段:
"从此,济南是一个与你有关的城市。我远远地逃开了那个城市,去了南方。有好几年,即使要乘飞机,要转车,我也尽量绕着那里走。那个城市很热,很无情,是地图上一块疤。泉城广场是一个笑话,我是那笑话的中心。但是造化弄人,有几年我不得不经常去济南,所幸我去的是济南的西南角,远离当年事发的东北角。西南角是很多部队的驻地,有千佛山和英雄山,没有你的痕迹,我在济南读书时,也只有清明节集体扫墓时去过那里几次。对我来说,那里像一座新城,一个也叫济南的陌生地。从此,济南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座城,它们咫尺天涯,势不两立,我要去的是西南城,一个与你无关的城……
我们从校门进去,穿过法律学院和一片小树林,越过桥,走过海报栏,来到宿舍楼和食堂……校园里到处是人,我失神地躲闪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歌声像从天外传来,漫过树梢和楼顶,将整个校园沐浴在一片祥音中,年轻的人们在歌声中来来去去,脸上带着明亮的笑,只有我,落魄得那样突兀,像是从全世界走散的那个人……"
问: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提高写作水平?您能否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寄语?
年轻人肯定有更高级的方法,我的建议会比较笨拙和老派,非要提的话,只有一点:不要只做知识和信息的搬运工,放下手机,到人群中去,去见识第一手的世界。我的微信有一句签名:偶尔写作,经常思考,时刻体验。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与学弟学妹们共勉。


